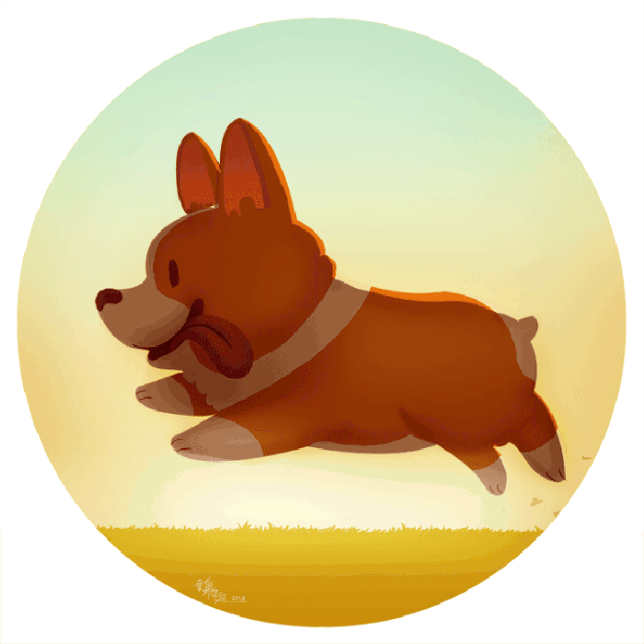【摘要】 杰夫·贝佐斯乘坐“新谢泼德号”,和兄弟马克·贝佐斯、一名 18 岁荷兰少年奥利弗·戴门,以及一位 82 岁女飞行员沃利·芬克一起到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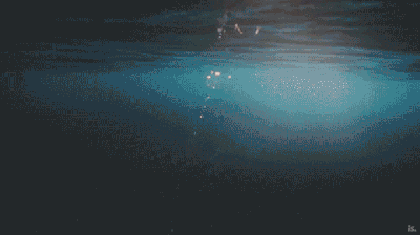
杰夫·贝佐斯乘坐“新谢泼德号”,和兄弟马克·贝佐斯、一名 18 岁荷兰少年奥利弗·戴门,以及一位 82 岁女飞行员沃利·芬克一起到达了太空。
而维珍银河创始人理查德·布莱森,在贝索斯上太空的9天前,就已经搭载维珍银河的“太空船二号”抢先一步抵达太空,体验了 4 分钟失重的感觉。
马斯克旗下的SpaceX也在维珍银河与蓝色起源之后,宣布将在9月中旬送4位“平民”实现太空之游。
贝佐斯曾在2019年就指出维珍银河还没有飞越卡门线。而这一次,布莱森还是没有冲破卡门线。
尽管Space X创始人伊隆·马斯克宣称将在2030年移民火星,但是他还未亲自进入过太空。
不同于其他两个玩家,太空赛道中的头部玩家SpaceX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新一波太空旅行的主导者不再是NASA,越来越多的私营航天正在扛起大旗。
越来越火热的太空赛道
3家公司中规模最小的维珍银河,只拥有1000位左右员工,并且亏损严重陷入资金黑洞。
全球首富贝索斯一手创办的蓝色起源则不愁资金问题,如今公司规模在3500名员工左右。
3家公司中规模最大的SpaceX有近万名员工。
20年前的马斯克在太空领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白,为了“火星殖民”的远大理想,在东欧国家手中买了火箭发射器后,研发出的猎鹰火箭已经成为 世界上最便宜的火箭。
这样的价格对普通人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但包括数名中国富豪在内的全球富豪已经开始排队买票。
2021年,1月14日,“女版巴菲特” 凯瑟琳·伍德旗下方舟投资计划推出一个“太空探索ETF”,代码为“ARKX”。
分别有轨道航天类股、次轨道航天类股、促成科技股、航天收益类股。
去年全球的投资者一共投入280亿美元用于民用航空领域, 太空旅行市场未来20年将从如今数千亿美元的规模增至一万亿美元。
美国富豪钟爱航天领域,离不开美国政府从小布什时代起放开的相关领域政策。
NASA更专注于学术研究,这也给精英企业家们留下了未经开辟的太空商业领域的空白窗口。
但是中国的民营航天基本都属于“新势力而缺少超级富豪,不同于追寻太空梦的贝索斯、马斯克,国内的超级富豪们还在绞尽脑汁赚钱。
世界首富贝佐斯这次太空之旅首次突破“太空的起点卡门线”。
而第一个到达太空的布兰森的飞船高度低于卡门线。所以布兰森的成功试飞招来了蓝色起源的“嘲笑”。
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乘客体验相差不大。但布兰森的“团结号”采用的是空中发射的火箭飞机,而贝索斯的“新谢泼德号”采用的是可重复使用的传统火箭。
“新谢泼德号”还比“团结号”多出一个应急逃生装置。此外,“新谢泼德号”采用了没有驾驶装置的无人驾驶太空舱设计。
两次飞行的人员构成也不一样。
不同于“团结号”飞天的都是专业的,“新谢泼德号”是纯“平民”参与。
太空旅游不算是新鲜事物。美国富翁丹尼斯·蒂托早在20年前,就已经花费2000万美元上了国际空间站。
光看价格,目前的太空旅游还只是有钱人的游戏,普通民众要实现太空旅游还是天方夜谭。
这次乘坐“新谢泼德号”的土豪花了2800万美元,而没有过“卡门线”的维珍银河的船票约20~25万美元。
太空旅行除了贵,还不安全,太空旅行爆炸、失联事故频发。
大多数航天员上太空之前都要经过数年的训练,而贝佐斯一行人只要14个小时的训练,对于非专业宇航员来说更友好。
普通民众要想实现太空梦,首先要让太空之旅像坐飞机一样实现航班化,价格降到和机票一样,其次是进一步提高安全性。
尽管真正的太空旅游时代还很遥远,但航天的商业化会把更多人带上太空。在未来,人们可以走的更远,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烧钱无底洞
美国不遗余力的推动太空领域商业化,这些首富与亿万富翁追随儿时的太空梦,纷纷创办商业太空公司。
首富们的太空梦一定离不开对自己儿时对火星、月球着迷的故事,同时有着在火星上建立一个自我维持的城市,保证生命的延续、防止人类的自我毁灭这样高大上的理想故事。
但一家太空公司的经营不能只有故事,过去十余年,随着烧光巨额的财富,挖走顶尖的科学家,才有一次次的火箭升空、宇航员飞天。
太空领域离不开融资、拿补贴,和创始人的自掏腰包。
尽管每一次太空旅行都可能是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但亿万富翁们还是争先恐后的上太空。
亿万富翁们都有着对太空的浪漫向往。
以特斯拉老板闻名的埃隆·马斯克,也是SpaceX公司的掌门人。2002年成立的SpaceX将目标指向了月球旅行。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就在SpaceX诞生的两年前,创立了蓝色起源。
亿万富翁的童年都离不开太空。
马斯克在童年时沉迷《银河系漫游指南》,也热爱《星际迷途》里描绘的世界。
小时候的马斯克就已经萌生了移民太空的念头。
贝索斯从5岁开始便对太空产生兴趣,在电视上看到阿姆斯特朗踏上了月球后深受感染。
理查德·布兰森在追逐太空梦前,其曾试图创造长途气球飞行纪录并因此遇到数次事故。
富豪们除了太空旅行还在考虑太空挖矿。
2012年,行星资源公司成立。股东名单十分豪华,包括谷歌CEO拉里·佩奇与董事会主席埃里克·施 密特,Word之父查尔斯·西蒙尼。
行星资源公司的目标是开采小行星的水资源、贵重金属。
太空商业化始终逃不开一个“钱”字。
尽管亿万富翁们财大气粗,但未来他们依然有可能要为资金的捉襟见肘发愁。
首富们是各自旗下太空公司的最大代言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放弃太空梦,而是会带领着更多人实现太空梦。

国内民营航天的内卷与春天
回到国内,中国在航天航空领域的中国速度都让人惊叹。
2012年中国嫦娥三号在月球登陆成功,2019年嫦娥四号首次着陆于月球背面,嫦娥五号去年成功在月球正面带回两公斤样品。
载人登月则是计划在2030年之后实现。
中国自主发射的“天问一号”让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部署火星车的国家。
当中国神舟十二号飞船成功将三名宇航员送入中国自己的天宫空间站时,老古董的国际空间站正在摇摇欲坠。
美苏之间轰轰烈烈的太空竞赛带来了进步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拖垮了两个世界霸主。
美国从此认识到了商业化太空的价值和重要性。
未知的太空,是人类最后的 " 新大陆 "。
中国有四大发射场、俄罗斯有三个、日本有两个、欧洲一个、印度一个,美国常用的只有卡纳维拉尔角和范登堡基地两处。
但是中国四大发射场并不开放给国内商业航天,所以民营太空的创业者只能自己建设商业发射场。
美国航天企业能享用的 " 航天资源 " 则充裕的多。
美国政府为了扶持马斯克和贝索斯的 太空事业可谓是 " 掏心掏肺 "。
从技术转让、人员帮扶,到新技术研发、发射场使用权等等资源,美国政府都大方放开,就差手把手教人造火箭了。
美国之所以如此重视商业航天,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垄断航天发射市场会导致发射成本虚高。
虽然中国新基建去年纳入了卫星互联网,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航天,但是重视不能让中国商业航天企业一夜之间长大。
当然,从国内 " 薇娅卖火箭 "、"B 站发卫星 " 这些出圈的事件可见,国人对这个行业的火热和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2014年是一个转折点。
在此以前,“商业航天”一词在中国还未被正式提出。
从2014年开始,国家频繁推出利好商业航天发展的文件与规定,航天产业对民间资本敞开大门。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去年商业航天领域投融资热度依旧不减。
尽管在融资事件数上较上一年减少36%,但融资金额首次突破100亿元,达到103.69亿元,相较2019年增长了61.21%。
我国商业航天市场的行业洗牌也早已开始,当一部分公司走向沉寂,随后很快就会有新的公司进入。
2018年航天企业注册量首次突破1万家。七年来企业注册量的高峰期在2019年,全年共注册了3.13万家,去年企业注册量有所下跌,全年注册量为4600余家。
残酷的一面是,“某企业信息查询平台”数据显示,8.5万家注册的航天企业中,其中状态为“存续、在业”的仅剩3.8万家。
虽然我国航天产业引入了更多民间资本,但这个赛道对于技术要求高、投入资金多,投资回报周期长也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国外商业航天史已有数十年,而6岁的中国商业航天,在经历即将到来的内卷期大洗牌后,则有足够的潜力挑战国外商业航天。